| 张家界旅游网--是张家界领先的旅游信息提供和服务商官网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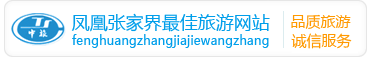 |
| 游客评价 |
| 攻略评价 |
打杵
白族村寨山多路陡,民家佬又喜爱背背篓,载运粮食和重物,可歇脚离不开垫凳。若过一截平路,背篓客气喘吁吁,谁充当民家佬的省力器?
打杵应运而生。
打杵,形状为“丁”字,横档歇背篓,竖杆戳地当支撑棒。打杵做法简单,找一根形似“丁”字的硬木树,稍稍加工即成。木匠师做打杵,只将一根横档与竖杆连接紧凑。打杵的作用就是省力。无论背篓客走平地或上高山,想舒服,只将打杵往屁股后一塞,背篓就有了依托,重量就全负荷在打杵上。想走,只须轻轻一抽。
在白族村庄,用不好打杵的背篓客,是当笑柄的料。用打杵也讲方法。打杵脚要找在一个平坦的地方,若杵不稳,或杵在岩尖或坑中,背篓的重力失控,极易造成“篓翻人打滚”的糟糕局面。找准平衡点,双腿撇开要适宜。撇宽了,卸了横力,起步耗劲;撇窄了,重心又不稳,稍稍打忽闪,背篓摇摇欲坠,让你大惊失色。歇打杵时,必须空出一只手护着打杵,固定力的方向,不然,腰一动,杵一颤,背篓席折断,随行者会惊叫:“拐哒,拐哒,××打杵翻蔸了!”
打杵,是最易使用最省力的劳动工具,白族村庄家家户户备用打杵。老人用细打杵,男人造粗打杵,小孩备短打杵,高个子拿长打杵。女人爱美,打杵也别致,在上面刻图案或雕字,再抹些桐油,油光发亮。许多后生爱物及人,趁女主人打柴,悄悄将打杵藏起,寻不着打杵的女人放高嗓吼:“你这饭桶,连女人打杵都偷,你将偷一世的打杵,背一世的脚,当一辈子苦力……!”
打杵是背篓的得力助手,成为人们不可多得的工具。腿受了伤,打杵当柱路棒,赶场逛闹市,遇上小偷或流氓,打杵又成为少林棍,田间地头捞渣草,打杵又当竹叶钯。打杵,这个木质农具,是白族人勤劳的象征,也是白族人智慧的结晶。
拗肩
拗肩是何物?北京的一位民俗学家,曾经打电话向我讨教。我向他解释说,拗肩,就是一根带丫的棒子,在搬运木料时靠它来泄力省劲。可到底怎样“拗”?我茫然无知。
后来我翻开书本,获知,拗肩乃白族山区扛木料时的省力器。使用拗肩时,可左右开弓,将拗肩的丫字头戳进木料下面,另一头用力往上翘,压在一个肩头的重力就被泄散,一部分重量随拗肩转移到另一个肩上。
书面的解释让我费解。在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天,我到麦地坪青峰溪村庄,体谅拗肩的作用。农夫瑛伯拿出拗肩让我尝试。这是一根粗大闪亮的拗肩,米把长,鸡蛋宽的丫口。
第一次用拗肩,感觉很神奇。又粗又长的木棒压在肩头,靠拗肩轻轻一“拗”,人轻松多了,走路也有力了。
神奇的拗肩还在于它能撑木料,让你挺腰昂头舒舒畅畅的喘气,若在平地,找不到搁处,你不得不扔掉木料。而再次搬运,你得费双倍气力。我不信,将木料“嘭”一声扔掉在地,再上肩时,感到一阵眩晕。这就是没用拗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瑛伯拿出另一根拗肩,说:“怎不用它试试!”
一根200来斤重的松树搁在我和瑛伯肩上。走到一丘田边,瑛伯说:“拗一肩!”我迅速使用拗肩,感受只背几十斤重量。走到一个上凸边,瑛柏又说:“拗一肩--歇!”两根拗肩杵在地上,我和瑛伯稳稳操纵着,像熟练地操纵一部电脑。木料服气地横在我俩身边,瑛伯又说:“扯拗肩--走!”那拗肩又发挥了它的潜力,几公里山路,我俩运用拗肩,时走时歇,时拗时扯,省力又省时,几歇功夫就将粗大的木料运到剧木场。
“拗肩就是铁臂阿童木!”我这样向北京的民俗学家解释。
湾架子
我们白乡村寨有谚语说:“铁架子,木架子,不搞我的湾架子!”这里的“湾架子”是一个俚语,指玩花样。而我说的湾架子,是由背篓席和木架构建的一种特殊的省力器。
背篓席穿在木架子中,木架的两根枋紧塞背膀旁,架上再造个“U”形状的卡口,这就是有名的湾架子。“U”形卡口,放木柴、粮食、烤烟、辽叶等,篾席绕肩,作背带。木架,又牢又硬,好固定;篾席,又轻又软,背着舒实,这种软硬相间,由竹和木巧妙构造的器具,湾架子就在崇山峻岭中世代穿行。
我在一个叫横堂湾的白族村庄采访,湾架子吸引我的目光。一位叫谷吉的老红军,见我热爱湾架子,将他藏在木楼里的湾架子赠给了我。
这个湾架子灰尘满面,却让我爱不释手。木是茶木,篾是南竹篾,整个湾架轻巧耐用,那“U”字架滑光锃亮。老人告诉我说,这个湾架子,曾经因背人立下了战功?
“背人”?我第一次听说湾架子的另一种作用,而“立战功”不得不让我对这个湾架子肃然起敬。谷老人说:“因为湾架子稳当,背人更方便,人只需两脚朝架上一夹,背着就跑,上山下岭比担架更实用!”老人告诉我,“那是大革命时期,我们村庄藏了23名红军伤员,刚开始,敌人搜山,我们只好用湾架子转移,在崇山峻岭中同敌人捉迷藏,湾架子好使,一个人可背一个红军,而担架要两人抬,且上坡下岭易翻滚,我们村用23个湾架子背红军,逃过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追捕!这湾架子,功不可没啊!”老人的话,让我对湾架子产生了深厚兴趣。
爷爷告诉我,他年轻时背脚,就用湾架子。我小时也用湾架子背柴去市场卖。我父背炭,在湾架子上耗费10个春秋。
如今,我们白乡,湾架子踪影全无。公路通了,车轮代替了脚步,机械代替了人力;作为运载工具的湾架子,也躲进旮旯里尘封起来。但对湾架子的记忆,我一点也没有尘封。昨天,又在邻居家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湾架子,尽管篾席不再牢固,木架不再沉稳,但那熟悉而亲切的模样,让我领略到他昔日的风采和神韵,我要将它发到网上去,告诉网民:湾架子是我们白族人民的忠实伴侣,因为它,背负着一个伟大民族坚贞不屈的历史。
| 三日游 | 公司荣誉 | 联系方式 | 付款方式 | zhangjiajie | 张家界旅游团 | 贵宾留言 |
| 张家界(000430)深上市子公司-张家界中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保证 7*24小时 400-000-3577 TEL:0744-8355777 8277999 8203888 8863888 FAX:0744-8279777 张家界旅游网 Copyright © 2000-2021 www.zjjo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张家界 张家界旅游攻略 张家界攻略费用 张家界旅游报价 张家界玻璃桥 长沙会议 Zhangjiajie 张家界攻略 张家界攻略 张家界旅行社 張家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