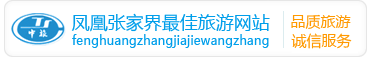黄狮寨上铺电缆的人
作者:杨幼园 来源:张家界日报
三年前,我上过一次黄狮寨。那次登上这个偌大的空中台地,不像今天有许多朋友相拥,热热闹闹。那年,我和在某酒店打工时结识的小刘与小胡,在黄狮寨索道下站门前“梅园”招牌后面的丛林里忙乎着,把一根根母指粗的黑色的电缆用泥土埋好后,小刘抹一把热汗对我们说:走,上黄狮寨!我说:怎么上?是乘缆车吗?记得二十多年前初上黄狮寨,我是和同事们从前门山道上爬上去的,那个累啊,回家几天腿还痛啊,至现在还记忆犹新。小刘说,当然坐缆车,免费的!
我下岗后到某酒店时,小刘和小胡已是老员工了。小刘来自桑植的大山里,读了些书,眼睛不太好使,戴着一幅黑眼镜,身材高高瘦瘦,面相秀秀气气,头发也梳理得利利糊糊。他处理工作问题毫不含糊,也有能力一个个解决好。我们一遇到难题都找他拿主意。而小胡就不同了。他虽说和小刘一般大小,都只二十多岁,却像个猛“张飞”,做么事都只图个痛快,却不讲究方式方法,喜用蛮力。他的长像倒与他的行事作风对得上号,面皮粗砺,浓眉大眼,腿短胳膊粗的,与小刘站到一块儿,让人禁不住发笑。
此刻,他俩就倚在缆车里的扶手上,有说有笑。我却对他们的奇妙组合不再感兴趣。随着缆车的冉冉上升,我如痴如醉似地饱览着窗外的奇异世界。那些刀削斧砍般形成的石柱子,就在眼皮子底下缓缓移动,甚至连它们身上乱如麻丝的纹脉,也一线线看得很真切。那一团一点附在石隙上的绿,历经风吹雨打,仍活得有滋有味,鲜亮无比。小刘笑说,是第一次坐索道吧?我说,是呢,是呢。这要感谢小胡。要不是他犯粗枝大叶的毛病,拉下电焊条,我哪来这飘飘欲仙的机会。小胡嘿嘿地笑着,脸上呈现出一丝无奈的神色。
随着缆车轻微地晃动一下,这辆专为我们运行的缆车稳稳地停下了。走出上站,走在这个凸起的台地上,发现二十多年前的一派杂乱、拥挤,已变得井然有序,该亮的地方亮得扎眼,该阴的角落阴得舒心,一根根合围粗的杉树直指蓝天,一条条规整的游道通向林荫深处。或许是淡季的缘故吧,游人相对我们第一次来时要稀少,因此寨子上面一片寂静,似乎落叶坠入地上的声音也听得清楚。小刘说,来一次忙紧架不起势,你就自个儿随意看看吧。我们要工作了,得抓紧时间把这根电缆埋到“天桥遗墩”边,然后焊接避雷地线。说罢,小刘和小张扛着焊机和一大圈电缆,踩着厚厚的落叶,往林子深处去了。
我独自在环寨游道上走着,每到一处观景点都注足默默地凝视,面对这旷世罕见的山的形象,内心总会有一种莫名的震撼,让我久久无法安宁。这种来自心灵的对我而言难以言说的不平静,即便时间又过去三年,到了2009年元旦,仍依旧难以平复。此刻,就在新年的第一天,我挺立在“天桥遗墩” 对面的观景台上,我的朋友们已经顶着寒风,踏着残留的积雪,兴奋地小心奕奕地观前面的风景去了,而我却迈不开脚步,仿佛有一股力量牵扯着我,让我鼓不起离开的勇气。这股神力是什么呢?我思索良久,似有所悟,它或许来自右前方那根竖立在悬崖边的监控探头吧!
这个把黄狮寨最美的景色,传输到世界各地的“探头”,便是当年我那两个朋友冒着生命危险安装的。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忙碌的身影,事隔三年,仍那样清晰可见。当时我从一个个观景点走来,到“天桥遗墩”时,他俩刚好埋着电缆钻出林子,头上都粘了武陵松松针,衣服上也尽是泥巴和落叶。稍事休息,他俩又开始忙活了。小刘整理着一根根地线,小胡挥舞着锄头,在板结的坡地上使劲抽槽,以便把避雷地线埋得更深一些。可就在小胡挥锄猛干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小胡用力过大,脚下一滑,竟顺着徒坡滚了下去!我的个天啊,下面若没有一个小平台,小胡便要一下子掉入万丈深渊,或可化为“天桥遗墩”的新一个墩子了。当我和小刘用电缆线把小胡拉上来时,相信我们的脸色都骇青了。可小胡却没事似的,呵呵一笑,又挥锄猛挖了——这个愣头青!
自此后,我再没见过小胡,听说他在武陵园当过包工头,还承包过某酒店,结了婚,媳妇生了个和他一样壮实的胖儿子。而小刘倒见过两次。一次他从长沙回来,取某酒店的安装图纸;另一次却见他抱着儿子,在市内一家规模不小的五金店里,背靠着沙发打瞌睡。那一次我没上前打扰他。
或许,他们已忘记了当年黄狮寨上惊人的这一幕,而我却不曾忘记,就像我无法忘记眼前这一根根或高或矮、或粗或细、模样百出的石山。生活并非都轻松,有时更像山一样沉重,还伴随着呜鸣作响的松涛声。如我。但我总不能在此停步不前,我得奋力赶上前,和朋友们一道前行。
因为,最美的风景,永远在前头。因为,有朋友做伴,你不再孤独。
网友评论
张
家
界
旅
游
网
张
家
界
领
先
的
旅
游
信
息
提
供
和
服
务
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