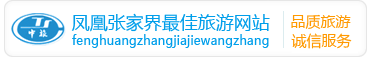|
大碗酒
大碗大碗酒,满满盛上;大碗大碗酒,满满端上;大碗大碗酒,满满搁上;大碗大碗酒,高高举上;
“逮--!”
慢饮,粗饮,狂饮。山醉,水醉,屋醉,人醉。
酒是山村里出名的酒。张家界人靠着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酿酒技术,靠着祖宗赏赐的那间土屋,挑澧水山泉,碾自家的粮食,摘屋后的药草,酿出那种外人尝试后打眯眯笑的土土的酒。酒,都有一个动听的名字:“苞谷酒”、“薯酒”、“米酒”、“高粱酒”、“枣酒”、“金樱子酒”、“金银花酒”、“三百棒酒”…….偶尔也有外来酒,但总没有山里酒醇香,总没有湘西酒清纯,湘西酒依然那么撩拔人。湘西酒是最劲大的酒,最烈性的酒,最醉倒人的酒。上了桌,男人的豪气开始显露,碗要大碗,大碗才尽意,大碗才代表湘西人的粗犷和坦诚;酒要烈酒,烈酒才过瘾,烈酒才代表湘西北张家界人的豪爽和纯朴。
碗,不叫碗,叫陶钵,专人盛酒的器皿。一钵酒,少则半斤,多则一斤,清清亮亮的酒搁在碗里,烈烈火火的酒泡在碗里,主人按湘西酒规先敬,一扬手,大碗大碗酒倒下去;客人也学,一仰脖,大碗大碗酒倒下去;陪客的张家界男人女人,一伸颈,大碗大碗酒倒下去。又一碗一碗的盛上,一碗一碗的摆上,互相看着,互相端着,互相笑着,再咕噜咕噜,好一个湘西北的英雄汉,好一个湘西北的大碗酒。
张家界男人酒量大,大碗大碗酒尽管醉,那是假醉;尽管烈,那是假烈。男人醉了,心里没有醉,那种微熏微醉的模样,那种微熏微醉的神态,那种微熏微醉的脸膛,种微熏微醉的感觉,还有那种微熏微醉的语言,代表着喝酒人最高的境界。张家界男人有着过多的酸楚,他们世世代代在恶劣的环境里土中刨食,顽强的生活着,用坚硬的脊梁挑着风风雨雨,带着家庭走,拖着家族跑,拉着历史行,背负社会的重任一路向前冲。大碗大碗的酒,大碗大碗自酿的烈酒,解馋,过瘾,来尽,爽气;无人作陪时,独饮,叫“喝冷当子”,依然大碗大碗,有人作陪时,叫 “喝团罐子”,还有“喝散酒”、“喝早酒”、“喝午酒”、“喝晚酒”、“喝花酒”、“喝交杯酒”、“喝歇气酒”、“喝出征酒”、“喝庆功酒”,大碗大碗喝酒,成为张家界男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大碗酒成为男人身体里的一碗碗血液。
刚出生,喝出生酒;洗三时,喝洗三酒;报喜后,喝祝弥酒;满月后,喝满月酒;一岁时,喝抓周酒;升学后,喝状元酒;立屋时,喝上梁酒;买房时,喝热火坑酒;定婚时,喝定亲酒;发八字时,喝请媒人酒;打嫁奁时,喝配木匠酒;结婚时,喝喜酒;探亲时,喝回门酒;粮食丰收,喝 尝新酒;过生日,喝寿酒;人归土后,喝送葬酒。大碗大碗酒,陪伴湘西人的每个不平凡的日子;大碗大碗酒,滋润湘西张家界人每个多情的日子。
喝下这一大碗一大碗酒,我何时能醒过来?
家里的麦子要我去收,田和地要我去耕,妻子的鞋和衣要去买,那娃儿的尿布要我去换,还有那扇石磨等我去推……
大碗肉
大碗大碗肉,冒着热气;大碗大碗肉,张着嘴巴;大碗大碗肉,饱在心里。
张家界人吃大碗肉很有名气。我居住的白族村寨,个个都是吃大碗肉的好手。特别是在宴会宾客,能吃大碗肉的人是众多客人中最受主人看中的角色,端菜的伙夫上一大碗肉,看谁先动筷先动嘴,一大碗肉见了底,伙夫会对房的掌厨说:“今天遇到个吓(白族话指厉害)家伙,逮肉象喝酒!”掌厨笑:“几把牛草胀得死牛?一个字:涨!”涨,就是涨肉,即添加大碗大碗肉,掌厨亲自端上桌,手一扬热热打招呼:“逮——!”鼓励那位被称为“牛”的吃肉客大口大口吃肉;也许好久没有吃到梦里都想吃的好肉,也许因为远途爬涉早已肌肠辘辘,也许因为掌厨的手艺太到位,牛肠马肚的吃肉客嘿嘿笑,很豪爽地应道:“逮就逮----!”遇到另桌的吃肉高手,几条汉须按行规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吃肉大赛,由主人做证,看谁面前的大碗肉消得快,最后主人还笑嘻嘻问最后一位吃肉汉:“还逮不逮得?”吃肉汉骄傲地拍拍肚子,响亮回答:“逮?再逮你家还要杀头猪母娘!”吃肉汉有了名气,遇到谁家媳妇生小孩,踩生当了“踏爷”按白族风俗要“胀踏爷”,被人请去吃,当然仍吃大碗大碗肉。
张家界大碗肉是出名的好吃。肉,是最上等的,质好,色美,味香;大碗肉中最受欢迎的是“肥片子猪肉”巴掌大,巴掌厚,巴掌长,讲究一块是一块,讲究一碗是一碗,讲究打退不如吓退,讲究谁吃得谁就做得。特别是到了栽秧季节,每家每户都办大碗肥猪肉,最大的一块有半斤,盖在大碗上,叫“盖面肉”谁吃这块肉,代表栽秧中的最好手,要去“插头艺”若谁不懂,悄悄偷吃,就犯了禁忌,这天栽秧要硬着头皮“插头艺”,插不赢,被关在田当中,叫“关笨猪”颜面大失。大碗肉中还有蹄子肉、坨子肉、寇肉、瘦肉、渣那肉、熏肠肉、腊肉、条条肉,就肉的种类分,还有羊肉、狗肉、鸡肉、鸭肉、鹅肉、牛肉、鱼肉等。
张家界大碗肉,是过好日子的一种向往。在旧时,谁家宴客有大碗肉,谁家就成为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谁家就会被人羡慕。一些手头紧的人家,在宴客时也会象大户人家一样摆上大碗肉,只不过在碗底用些辣椒作垫,上面仍铺着一块块大肉,遇到能食肉的汉,几筷子就把贫困的家底给揭穿。
张家界人都爱吃大碗肉。小时候,我们参加大人们的宴席,上桌第一件事就是抢那碗大块肉。在偏僻的山寨,主人聘请农工,一律用大碗肉宴客,一则显示主人家的豪爽大气;二则检验农工会不会吃肉,有不有气力干活。那主人的话说就是“吃得就做得,你想想,一个大男人,胀不得几大碗肉,那几百斤的担子还不把他压瘪?”当然,胀得几大碗肉的汉子很快被选上。也有吃的几大碗肉的莽汉被选上后,干活时像坨稀泥巴,软绵绵的。晚上,主人仍用大碗肉宴请,莽汉一点也不推辞,吃的满嘴流油,主人笑着说;“你为何这样吃得?” 莽汉答:“你看——我好大个壳廊!”主人笑问:“你为何又这样无力?” 莽汉答:“你看——我生得好软戳!”。
父亲对吃大碗肉特别挂念。责任制下户那年,我父亲到一家有丧事的户里帮工,解斋后,督官喊:“散斋喽!逮大碗肉!”父亲欣喜若狂,与几个庄稼汉坐在八仙桌上,吃相很粗俗,吃得满嘴冒油,满桌流油,满地掉油,满身糊油,满手满嘴满腮满碗都是油,一滴滴香喷喷的油!母亲站在屋檐下,静静地看着父亲大块大块吃肉的俗气相,流下泪说:“都怪我,没把家料理好,让你父亲没吃上几餐饱肉!”奶奶也看的发呆,说:“都怪我,这些年只顾捞工分,让我儿亏了生活,连顿像样的大碗肉都没吃过!”我知道,奶奶为了家,为了队上丰收,一生都没吃过饱饭饱肉。责任制到户后的第二年,我家杀了头大肥猪,刚把肉挂好,就传来独居的奶奶重病不起的消息,记得奶奶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嘴里还在喃喃的喊:“肉……大碗肉……大……块……肉……!”母亲把大块大块肉送到奶奶嘴边,奶奶又吃不下去,强吃就强吐,咽不下去,最后,母亲只好把大碗肉让奶奶闻闻,奶奶最终没吃上自家喂的第一头大肥猪身上的大碗肉就带着永远的遗憾告别人世。每次大年三十到奶奶坟前祭奠,我们要捎上一大碗肉,喊着奶奶的名字,叫奶奶“吃大碗肉”用这种无奈的方式,表达对祖先的思念。
大碗饭
“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
“虎很三声喊,人很三碗饭”
在张家界,吃不得三大碗饭的人,常被人瞧不起。
田处偏僻,山多路遥,吃不得几大碗饭,能有气力爬山涉水?能有气力侍侯庄稼?能有气力放排撑船?
为了这三大碗饭,张家界人每时每刻都在打拼,每时每刻都在劳作,想的是三大碗,做的是三大碗,给子孙留下的还是三大碗。三大碗中,最受人们喜爱的是“大碗米饭”米饭是自己田里产的,虽然每年只种一季,一季只收几百公斤,但人们对产大碗饭的稻田情有独钟。那丘田在岭端,瘦瘦的,很贫瘠,上摸得到天,下看得到谷底,有水就丰收,无水就绝收;可栽上秧,就有了希望,就有了盼头,就有了救命的大碗饭。田要犁三次,埂要糊三次,肥要施三次,水要放三次,半夜要趁雷雨季节赶“雷公田”。天下暴雨,决不能让水跑下山去,决不能让开裂的土再开坼;牛角上捆着火把,男人女人倾巢出动,人与牛在田里打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苦苦煎熬。
大碗饭的种类很多,味道美的有:小麦饭,薯米饭,洋芋饭,绿豆饭,高粱饭, 米饭,蚕豆饭,苞谷饭,荞麦饭……过苦日子时吃:厥粉饭,棕米饭,萝卜饭,白菜饭,葛根饭……最难吃的有:蒿子粑粑饭,棕子粑粑饭,野枇巴饭,芭蕉兜饭……这些“饭”野草野花野果为主料,煮成一道道有地方特色的饭食。在大碗饭中,最出名的叫“张家界粥”,“张家界粥”在过去贫困人家中充当主食,无福吃干饭,就只能喝粥了。当时有首《煮粥诗》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好商量。一升好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大碗粥是种对贫困生活的无奈,小时候,面对无米之炊的尴尬,母亲变些花样做粥让我们兄妹填饱肚子,我们不愿吃,母亲常教育我们“多吃萝卜菜,啥病都不害”还幽默补一句:“喝稀粥要搅,走滑路要跑”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后来遇到灾年 ,连大碗粥都喝不上,母亲总带着一份淡淡的忧伤说:“要是有大碗饭吃,我们该有多么幸福啊!”
人们对粮食的渴望和追求越来越 迫切,对粮食的生产、收割、储备、收藏都非常重视,每个环节都讲究精细到位。在撒谷种时,办“撒谷种节”。家家户户从吊脚楼取出谷种,用水浸泡,待芽生出,去撒种,手一扬,谷种撒下去,像撒一行诗歌;手一挥,谷种撒下去,像撒一褛春风;手一张,谷种撒下去,像撒一轮彩虹。家家户户要搬猪头肉祭祀一番;栽秧时,办“栽秧酒”大酒大肉 劳栽秧者,吹“栽秧唢呐”栽秧手在田间狂欢,相互用泥巴攻击,身上,手上,背上,脸上,腰上,腿上,头上,耳朵上,脖子上,鼻子上,嘴巴上……都糊满了泥,据说,泥糊的越多,大家越喜欢。泥,就代表一碗碗饭;泥,就代表一堆堆粮食。
“糊仓”的风俗让村民感收到了生产粮食的兴奋和骄傲;割谷时,办“尝新酒”主人先下田割第一蔸谷,亲自嚼响第一颗新米,朝众人喊:“我的田——谷多不多?”众人大声说:“多——!”又吼:“我的谷-——甜不甜?” 众人大声说:“甜-——!”再吼:“我的谷-——发不发?” 众人笑着大声喊:“发!发!发得——像猪母娘下包儿!”于是大家能吃到刚出产的大碗饭了;大堆大堆的粮食堆在塔里,大堆大堆的粮食搁在塔里,村寨到处弥漫粮食的味道。
因为有了大碗饭的条件,因为有了大碗饭的诱惑,我们从小品尝着大碗饭带来了喜悦,一点也不注重自己的吃相:到学校寄宿,食堂一打铃,我们拚命的往食堂跑,“嘭”一跤跌得人仰马翻,饭钵儿跌变了形,害怕别人将自己蒸的那大碗苞谷饭搬去,常故意不排队,使劲挤,挤的全身都有油和饭。端着碗,我们像群抢食的小猪崽,噜苏相让人吃惊:我们大口大口的吃,我们大口大口的嚼,我们大口大口的咽,或坐,或站,或蹲,或卧,或靠……刚吃完就趴在桌上打盹,老师爱讥笑我们不雅的吃相,常这样用打油诗嘲讽:“人是铁,饭是钢,吃哒还有半歇殃!”
张家界大碗饭,作为湘西各族人早中晚三餐的主食,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花样也时常更新,对家底不富裕的人家来说,吃大碗饭,是“糊口”,填饱肚子,不挨饿,主食不讲究,粗细都能吃。对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来说,吃大碗饭,是“大吃大喝”或“美食”,色、香、味全,甚至还讲究美器美餐,主粮精细,米要上等好米,还要煮上绿豆等以加强营养和口感,从饮食变成“文化”。张家界大碗饭,养活着湘西北一个个憨厚纯朴的乡亲,养活着湘西北一个个炊烟袅袅的村庄。
(作者:谷俊德) |